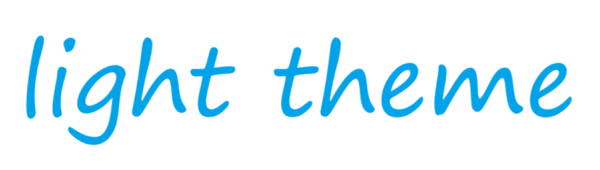本文引用:孙彩云, 林征, 周美景, 顾子君, 罗丹, 王咪, 顾珺怡, 朱展慧. 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获益感的潜在剖面分析. 中国全科医学[J], 2022, 25(06): 656-662
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2.085
SUNCaiyun, LINZheng, ZHOUMeijing, GUZijun, LUODan, WANGMi, GUJunyi, ZHUZhanhui.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Benefit Finding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J], 2022, 25(06): 656-662 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2.085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疾病,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1]。IBD好发于青壮年人群,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等肠道症状,且反复发作、迁延不愈,患者易产生多种负性情绪,这些情绪通过神经、体液免疫反应等多重环节扰乱肠道菌群,导致疾病复发或加重[2]。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发现个体在患病过程中除了产生负性情绪,还会对压力性事件进行认知重评,探寻疾病给自身带来的积极意义,即疾病获益感[3]。疾病获益感对自我管理行为和生活质量的正向预测作用已被证实[4],关注患病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可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并适应疾病。既往研究发现,高水平的自我表露和社会支持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疾病获益感[5,6]。然而,目前国内外鲜有报道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的研究,且现有研究主要依据得分高低判断总体疾病获益感水平,忽略了不同水平患者群体间的异质性。潜在类别模型则是根据个体在外显变量的作答模式来判断个体所属类别,并展现各类别的人数比例[7],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别的人群特点,实现精准干预。根据外显变量类型,可分为适用于分类变量的潜在类别分析和适用于连续变量的潜在剖面分析[8]。本研究旨在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究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类别及其特征差异,为制定提升该群体疾病获益感的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或住院的IBD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2018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制定的IBD诊断标准[1];(2)年龄≥18周岁;(3)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上,能阅读并理解问卷。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障碍或严重精神疾病;(2)患有恶性肿瘤、心肝肺肾等慢性疾病。样本量取变量数的5~10倍,且考虑到20%的失访率,总样本量至少为94~188例。本研究通过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审批号:南医大伦审(2020)594号〕,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
(1)潜在剖面分析法可以根据个体在外显变量的作答模式来判断个体所属类别,并展现各类别的人数比例,方便探究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获益感类别。
(2)分析不同类别患者的特征差异及类别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提升该群体疾病获益感的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实现精准干预。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用于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居住地、居住状态、职业状态、家庭年收入等人口学资料及疾病分型、病程、疾病活动度、使用生物制剂、该病相关手术史等疾病相关资料。
1.2.2 修订版疾病获益感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
BFS用于评估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感受到的益处,由ANTONI等[9]于2001年编制,后经其他学者不断改进。2018年边静等[10]针对中文版BFS中易产生歧义、不符合国内语言表达习惯的条目进行修订,形成修订版BFS,该量表含有接受、家庭关系、个人成长、社会关系、健康行为5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1=完全没有,5=非常多),总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疾病获益感越多。修订版BF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3,重测信度系数为0.884。
1.2.3 中文版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Berke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BEQ)
BEQ用于评估自我表露的内容性质及强度,由GROSS等[11]于1995年编制,后经国内学者赵鑫等[12]翻译回译及文化调适形成中文版。中文版BEQ包括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正性情绪表达强度、负性情绪表达强度以及负性情绪抑制5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其中条目3、8、9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越倾向于情绪表达。中文版BEQ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重测信度为0.53~0.63。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SSRS用于评估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由肖水源[13]于1994年编制,含有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第1~4、8~10条,选择第1~4项分别计1~4分;条目5中的4个子条目采用4级计分(1=无,4=全力支持),4个子条目总分之和为条目5得分;条目6、7,选择"无任何来源"计0分,选择"有来源"则几个来源计几分,总分为10个条目得分之和,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SSR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1.3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问卷由研究者发放与回收。调查前使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介绍本研究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要求,经患者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调查问卷由患者自行填写,患者对问卷表述有疑问时由研究者使用统一语句解答。填写完毕后现场回收,并检查填写质量,若存在缺项、重复填写等问题,请患者思考后再填写。剔除作答规律性强或明显随意勾选的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Mplus 8.3和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根据外显变量类型(疾病获益感为连续性变量),选用Mplus 8.3软件中的潜在剖面分析模块分析数据[8]。从单一类别模型开始,逐步增加模型中的类别数目,直至模型拟合指标达到最佳。模型拟合指标包括:①对数似然比检验〔Log(L)〕、Akaike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AIC)、贝叶斯信息标准(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BIC)和校正BIC(adjusted BIC,aBIC),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好;②熵(Entropy)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接近1表示分类越精确,当Entropy=0.8时,提示分类精确率>90%;③似然比检验(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用于模型比较,检验显著时(P<0.05)表示第K个模型拟合优于第K-1个模型。综合评价各类别模型拟合结果中的上述指标,选择最佳拟合模型。(2)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及患者一般资料
共回收问卷230份,剔除无效问卷4份,回收有效问卷226份,有效回收率为98.3%。226例IBD患者中,男157例(69.5%),女69例(30.5%);年龄(34.6±12.5)岁;学历为小学及初中46例(20.4%),中专或高中45例(19.9%),大专及以上135例(59.7%);未婚88例(38.9%),已婚136例(60.2%),离异或丧偶2例(0.9%);城市171例(75.7%),农村55例(24.3%);独居27例(11.9%),非独居199例(88.1%);在职165例(73.0%),离职48例(21.2%),退休13例(5.8%);家庭年收入≥5万元165例(73.0%),<5万元61例(27.0%);克罗恩病159例(70.4%),溃疡性结肠炎67例(29.6%);病程<1年68例(30.1%),1~5年133例(58.8%),>5年25例(11.1%);缓解期141例(62.4%),活动期85例(37.6%);使用生物制剂22例(9.7%);既往有该病相关手术史61例(27.0%)。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主要由患者自我报告,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4],结果显示特征值>1的因子共9个,且首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7.43%(<40%的推荐标准),提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IBD患者疾病获益感潜在类别及命名
根据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的评估结果拟合潜在类别模型,本研究共拟合5个潜在类别模型,各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1。模型3的BIC值最小,Entropy值最接近1,且LMR和BLRT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综合比较各模型间的拟合指标,以含有3个潜在类别的模型3作为最佳拟合模型。各类别的IBD患者归属于该类别的平均概率在99.3%~99.8%,表示该模型结果可信。
Table 1 Latent class model fit indicators for benefit finding
基于模型3,各类别在疾病获益感22个条目得分均值如图1所示,根据其特征分布分别对C1、C2、C3命名。C1类别的条目得分总体偏低,其中条目13~16得分结果提示该类患者患病后不知如何应对生活及工作、安排时间和处理压力,命名为"低获益-应对无力组",占比50.9%(115/226);C2类别的条目得分水平总体介于C1、C3之间,条目20、21分别代表患者患病后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的行为方式调整,两条目得分相差较大,命名为"中等获益组",占比28.3% (64/226);C3类别的条目得分总体较高,条目4~7得分结果提示患病经历使得患者明显感知家人的关爱,命名为"高获益-感知被爱组",占比20.8%(47/226)。
Figure 1
Figure 1 The characteristic distribution of three latentclasses of benefit finding among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2.4 IBD患者疾病获益感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三组患者职业状态、家庭年收入及疾病活动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居住地、居住状态、疾病分型、病程、使用生物制剂、该病相关手术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among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三组患者中文版BEQ及各维度、SSRS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 scores of Chinese Version of Berke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mong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2.5 IBD患者疾病获益感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以IBD患者疾病获益感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指标为自变量(赋值见表4)进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主观支持是IBD患者疾病获益感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5。
Table 4 Assignment fo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atent classes of benefit finding among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using ordinal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Table 5 Ordinal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latent classes of benefit finding among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3 讨论
3.1 IBD患者疾病获益感可分为三类,需重点关注低获益-应对无力者
本研究发现IBD患者疾病获益感可分为低获益-应对无力组、中等获益组和高获益-感知被爱组3个类别,提示IBD患者疾病获益感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
低获益-应对无力组患者占所有IBD患者的50.9%(115/226),该类患者在个人成长维度的条目得分明显低于总体水平,反映患者不能合理安排时间和有效应对压力,学业工作及生活条理性明显降低。由表2可知,相较另外两类,该类中离职、低收入、处于活动期的患者占比最大,印证了IBD患者因病程迁延反复需多次住院,部分处于疾病活动期的患者还需频繁请假,甚至休学或离职以配合疾病治疗,严重扰乱生活节奏[15],这可能也是该类患者无力应对工作、学业和生活的重要原因。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该类患者,介绍乐观且疾病控制良好的病友与其分享成功应对的经验,帮助患者正确看待疾病,不过分关注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注重提升疾病应对能力,同时指导患者掌握症状管理、压力管理等自我管理基本技能,实现有效应对。
中等获益组患者占所有IBD患者的28.3%(64/226),该类患者运动相关的获益感偏低,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患者缺乏疾病相关知识,担心运动会加重病情[16],或是知晓运动能够延缓疾病复发,却不知如何选择适宜的运动方案,从而更倾向于选择"静养"的方式。这提示医护人员应纠正患者错误的运动认知,为其制定个性化、具体可行的运动处方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或邀请有运动经验的病友共同参与,以增强运动给患者带来的获益感。
高获益-感知被爱组患者占所有IBD患者的20.8%(47/226),该类患者在家庭关系维度下的条目得分大多高于总体水平。在我国,家庭是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7],患病后其他家庭成员为患者提供的悉心照护、经济及情感支持易使个体感知到自身被爱包围,同时深刻认识到家人的重要性,进而激发患者与疾病抗争的信心。因此,医护人员可鼓励患者家属主动了解并满足患者的需求,鼓励家属一同参与患者疾病管理,以促进IBD患者对家庭支持及亲密关系的感知,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
3.2 不同疾病获益感类别的患者在人口学及疾病特征存在差异
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与疾病相关特征虽然不容易干预,但了解不同疾病获益感类别的患者间差异可帮助医护人员进行早期识别。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低获益-应对无力组,中等获益组和高获益-感知被爱组中的在职患者占比较高且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较好,与LI等[18]及桑明等[19]的研究结果相似。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获益-应对无力组中处于疾病活动期的患者较多,提示疾病活动度越高的患者,疾病获益感可能越低,这与长期前列腺癌幸存者的研究结果相似[20]。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21],躯体功能是保障生理需求的前提和实现高层次需求的基础。活动期IBD患者生理功能被严重损坏,频发的肠道症状使患者产生躯体失控感,扰乱患者正常生活。疾病活动度高的患者常需要激素和鼻饲管营养治疗,合并严重并发症的患者还需要造口治疗[1],这3种治疗方式常会引起身体意象改变。躯体失控感和身体意象改变易使新发疾病活动的患者感到难以接受和应对无措,使复发患者产生自我怀疑和疾病管理信心丢失,难以产生疾病获益感。但以上变量未能进入最终的回归方程,可能与本研究中等获益组和高获益-感知被爱组的样本量较小有关,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上述因素对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类别的影响。
3.3 自我表露有助于提高IBD患者的疾病获益感,鼓励患者表达疾病相关感受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组患者自我表露存在差异,正性情绪表达与负性情绪表达是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且正性情绪表达对IBD患者疾病获益感的影响更明显,该结果与乳腺癌患者的相关研究结果类似[22]。自我表露是指将个人经历、想法或内心感受与自己对话或与他人分享,实质上是将大脑中模糊不定的想法或观点转化为具体语言的过程,该过程使得个体对原来模糊、复杂和变化的信息进行认知重评,改变看待事件的思维方式并重新定义[23]。积极的表露主题可调动患者的正性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认为[24],正性情绪能够拓展思想和行为,帮助个体建立身体、智力和社会性资源,拥有这些资源将以间接方式使个体获益。因此,医护人员应提醒患者避免情绪压抑,鼓励患者多与他人沟通交流,且尽量表达疾病相关的积极感受,进行正性自我评价,从而增强患者对疾病的接受度和自身价值的认可度。书写表达作为一种表露个人经历感受的积极心理学干预方法,其帮助患者增强正性情绪的作用已在国内IBD患者群体中得到验证[25],且该方法有着经济、易实施、对干预者资质无特殊要求等优势,干预形式也符合我国含蓄内敛的文化背景,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3.4 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IBD患者疾病获益感,注重提升患者主观支持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组患者社会支持存在差异,且主观支持良好的IBD患者有着较高水平的疾病获益感,这与在糖尿病患者中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9]。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对客观支持的感知情况[13],即个体在社会中被理解、尊重和支持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这虽与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却是个体心理的反映,影响患者对疾病的适应[26]。根据缓冲作用模型,主观支持能够缓冲个体对负性事件的知觉评价和行为反应,从而缓解压力,实现适应性调整[27]。IBD患者大多为青壮年,正值学业、事业、家庭发展上升期,但罹患疾病给这些发展带来一定阻力和冲击,家人的开导和理解能使患者减少内疚感,并意识到自身背后强大的支撑力量,从而增强对抗疾病的信心。疾病症状会扰乱患者的工作状态、降低工作效能,患者感知到的同事帮助及领导关心不仅能缓解工作压力,更能促进患者向同事及领导袒露病情,减少自身病耻感[28],获取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此外,部分地区已将该病纳入"门慢""门特"之列,但仍有患者不知晓这些政策,长期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外界除了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客观支持,还需关注患者的主观支持情况。医护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需求,支持患者参与共同决策,鼓励家属多与患者交流,了解其内心感受并满足需求;学校及工作单位可为患者举办座谈会,结合患者需求合理安排任务,并提倡公众尊重、接纳患者;政府除基于患者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医保制度外,还需加大宣传以扩大患者对相关政策的知晓度,从而提升患者主观支持。
4 小结
IBD患者疾病获益感存在明显的分类特征,其中低获益-应对无力组患者占比较大(50.9%),且患者疾病获益感的影响因素包括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和主观支持。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低获益-应对无力患者,提升疾病活动期患者的应对能力和信心,鼓励患者表达疾病相关感受并促进患者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以提高患者的疾病获益感。但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无法确定上述因素与疾病获益感间的因果关系,且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可能存在信息偏倚的情况。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开展多中心、大样本调查,以进一步验证、完善本研究结论。
本文无利益冲突。
本文表格略。
参考文献略。